作者:张向前
来源:阿若文苑(微信公众号)
刊发于《川中文学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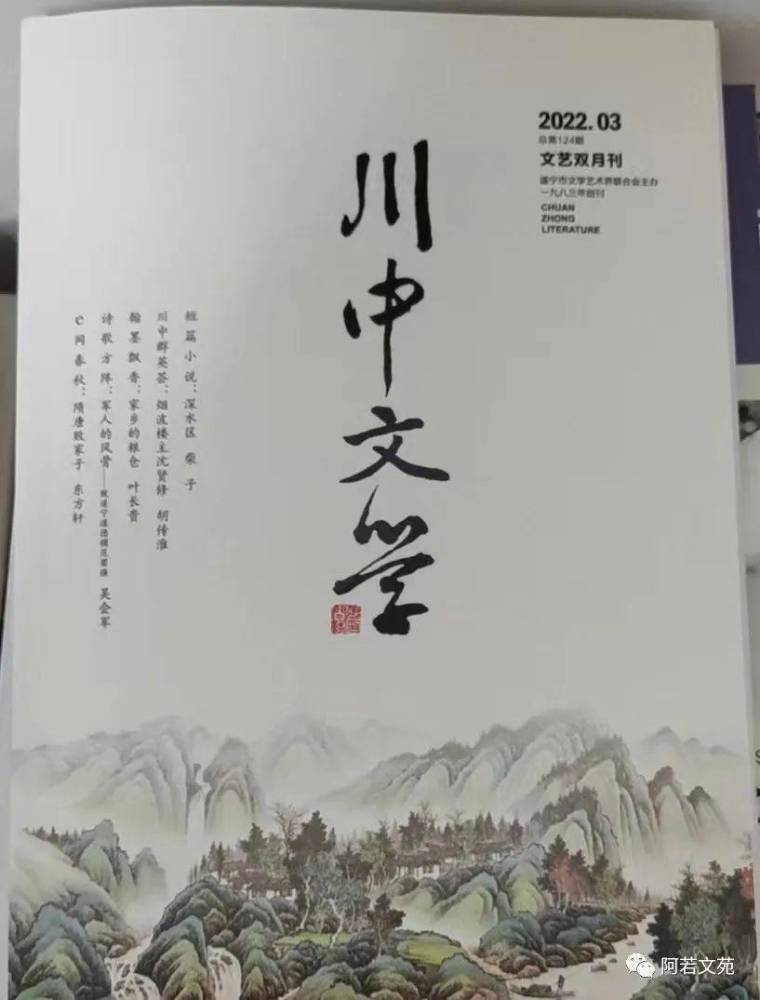
我从未想到,父亲会走得这么早。
三姐从老家四川打来电话时,带着哭腔。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,三姐一贯坚强,从来没这样悲伤过。
“癌症晚期?不会弄错了吧,父亲上个月在郑州身体不都好好的吗?”一个月前,三姐陪着父亲、母亲来郑州参加我热闹的婚礼。除了右臂膀有点疼,父亲一如既往地健旺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肺癌转移后导致的疼痛。
三姐的哭声在电话里传来。
这个噩耗来得太快,一下子把我整蒙了。天要塌了。挂了电话,我半天没有意怔过来。那时,我刚过而立之年,感觉并未真正“立”起来。“呼”地一下,父亲直接把这个家的重担和风雨都甩了过来。迅雷不及掩耳,我哪里招架得住?能力和思想似乎都欠缺储备与涵养。
尽管刚休完婚假,想起奶奶去世时未见最后一面的遗憾,我还是决定请假回四川老家一趟。
与平时里休假的心情完全不一样,想到重病之中的父亲,想到即将不祥的父亲,想到望子成龙的父亲……我泪如泉涌。
说来惭愧,自小手不能提,肩不能挑的我,真的没什么能耐,这让父亲很担心。担心我长大之后能不能继承他的家业,把这个家发扬光大——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姐妹们迟早是要嫁出去的,似乎只有我才能继承他的衣钵,发扬光大,并更好地传承下去。到我这一辈,我们家族已经是第三代单传了。他当然要想这个事,要认真地想这个事。这个事情不仅关乎他的能力,也关乎列祖列宗,他在心里无数次地拈量过这件事。
望子成龙,是每个中国父亲的愿景。父亲对我的最初的规划是读书入“仕”。
十七岁那年,初中毕业。和所有热血上进的莘莘学子一样,我怀抱理想,期望在学习的征途上过关斩将一帆风顺。考上重点高中,读个名牌的大学,然后当个老师,或者当个科学家。这是我们那个年代,所有有理想学子的理想。我也不例外。我一直是班里的班长,是学校第一届学生会主席。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,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,七门功课六门全班第一,总成绩全班第一,抱回七张奖状,父亲自然是乐开了花。按现在的话来讲,我是个“学霸”级的人物。照这样的发展趋势看,考上个好点的学校读高中,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
上学在乡里,中考在县城,相距有二十多里地。为了考试方便,我跟朋友小文借了一辆自行车。那天一大早,我骑上借来的自行车,兴冲冲地从家里赶往县城一中。心有理想步履轻。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就像哪吒的风火轮,在脚下尽情驰骋,仿佛我正通向成功之路。公路两旁的花草树木嵯峨苍翠,像列阵而待的将士。我没有心思理会它们,心里想着学校,想着教室,想着按准考证上的号码找到某个对应的座位,然后开始坐下来飞快地做题……
到县城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中和对应的座位。看见考生安静地坐在桌子前,有的沉默不语,有的似乎还有些紧张,也有的似乎故作轻松状。如此情形,我脑海中竟然浮出了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画面。开考的第一科好像是语文,我做得应该是比较顺利的,答完题检查完就提前地交了试卷。
我在街上吃了一碗正宗川味的麻辣兔子面,算是对自己上午考试满意的奖励。然后,我骑上自行车到我的大姐夫处去休息一下。大姐夫在县城旁边不远的果园里上班,骑车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我把车放在果园楼前的大门右边,便上楼去睡觉了。等我睡醒起床,下楼准备骑车去考试时,才猛然发现,原来停车的地方空无一物。“车呢?”我慌了,忙叫姐夫一起来找。可是,哪里还找得到。毛贼待我离开后,早已下手撬开车锁,骑着飞奔到别的地方了。说不定此时正得意呢。我脑子里一片混乱:丢了车怎么去学校考试,丢了车怎么赔同学的钱,那个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多元,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,严肃的父亲会怎么收拾我……

等我坐公交车,再步行好一段路赶到学校时,下午的考试已经开始了。监考老师很温和——那张和蔼的笑脸可以温暖我整整一生。听我简单地讲了情况后,她把我让进了考场。但成绩可想而知。接下来的几场考试也稀里糊涂地考完了……
考试成绩出来,除了第一科语文考试成绩还不错以外,其他的都较差,总分没有达到理想高中的分数线,但还是考上了两所中专技校,一所是美术类的,一所是财会类的。这当然不是我的理想。父亲不甘心,酷热的夏天,带着我去没有开学的学校考察,试图唤起我的进取心。大热的天,父亲穿着短裤,披着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衣,手里拿着一把蒲扇,兼作遮阴,或扇风。父亲走在前面,我跟在后边,无精打采地走着。仿佛是钦差押着罪犯前往别地。
父亲曾经当过教师,也知晓甚多。一路上,他跟我讲了许多道理和县城里的一些情况。可能是叛逆,也可能是执拗或倔强,我对那两所学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。知道已无可挽回,父亲不再劝说。我跟在父亲身后,亦无语。这种无语,默默地宣告我纯粹的学生时代终结。夕阳下,我看见父亲曾经像山一样的脊背,微微有些驼了。
那个时候,一些年轻人正在或者已经从土地上脱离出来,开始进城里打工,靠手艺在城里谋生、挣钱。我的二姐夫我喊二哥也夹杂在进城的人群中,他学的是木匠,同门师兄弟很多,相互帮忙或揽活一起做,是他们互相关照的默契。他和他的师兄弟们很快在这座省会城市站稳了脚跟。
父亲与母亲商量,让我去成都跟着二哥学木匠。父亲征求我的意见。闲散的我岂有不同意之理。
我初到成都的街头行走,东南西北不分。那时,成都的天空有点迷茫,我也迷茫。
我跟在二哥身后,背着背兜,里面装着斧头、刨子、锯条、卷尺等。左拐,右拐,直行,到了九眼桥附近的一个路边劳务市场。二哥拿出一些工具摆在路边,以此招揽生意。和我们一样做木工手艺的人不少,还有刷漆、砌砖等手艺人。那时的生意并不好,少有人问津。其间,二哥接了一个木工师兄的电话,问我能否找到回去的路,我点头,二哥便离开了。
天快黑了,没有接到活儿,我收拾工具返回。不知那儿拐错了,走岔了,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倒回去再重走,依然,往复多次。我坐在街边,无助地哭了起来。哭完了,再找。等我深夜摸到住处,二哥早已回家了,锅里煮着白米稀饭,水雾蒸腾。我的那颗玻璃心,比稀饭还要稀,还要碎。
我在成都大约呆了一个多月,就离开了。成都的天空没有表情,成都的阴雨也将我轻飘的脚步轻飘地抹掉,不留痕迹。
后来,每次从郑州回四川老家资中,我都会在成都勾留几日,但从未想去过九眼桥看看。我不知道那儿变了没有,不知道那儿是不是还有招揽生意的手艺人。岁月不羁,那是我生命折叠中的一颗肉色青春豆。
父亲决定亲自“带教”我。父亲没有技术,他只会勤奋地耕种土地。土地是他眼中的“宝”。物质生活的一切,他都伸手向土地要。土地对他也不薄,回馈他粮食、蔬菜,以及由这些东西换来的其他的物质。靠着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,父亲养活着全家9口人,日子过得有汁有味。
坦诚地讲,父亲应该算是一个优秀的庄稼人。“优秀”这个词用在庄稼人身上,好像有些不搭。父亲站在土地面前,比站在我面前更有自信。父亲腰板挺得直直的。他有理由骄傲。土地听他的话,给他丰厚的馈赠。我也听话——尽管有些叛逆,但从不敢顶撞父亲。当然,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总是落空,我没有成功地做成一件事,让父亲心里妥帖。我就像一块盐碱地,只投入不产出,他的两次心血都都付诸东流。当时的父亲不知道,他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白费,那些经历渲染了我生命的底色。学习让我了解世界,并成了我一生中每天坚持的习惯。学艺让我走出乡村的视野,以更大的视角从另一个侧面看待世界的不同,仰望城市的星空,吞吐云烟,并能将它们诉诸于文字而长久地回味缅怀。
第三次能成功么?父亲能把我带教成一个优秀的庄稼人吗。父亲似乎有信心,我却没有。我那时处于人生的低谷,做什么都没有信心。
翻地、点种、牵行子、打窝子、插秧、收麦、挖土豆、担红薯……这些活儿我都干过,不一定很精通,但我确实都干过。
“电桩土背面有一个大坑,泥土都被水冲走了,里面有块稍高的地方,裸露的红岩已风化得差不多了,你拿着小锤、錾子去开垦成地,将来可以种点庄稼。”
跟了父亲三个月,我开始独立作战。土地把父亲的岁月深深掩埋,一道沟,一道垄,一个坡,一块田……
桩土是离我们家在最远的一块地,在马道子上边,得有二、三里地。马道子是条马路。父亲说的那个大坑就在马道子和电桩土之间。我右肩扛着锄头,左手拿着小锤、錾子,迎着早上有点慵懒的阳光,往电桩土走去。
坑并不深,大约有一米多的样子,是流水长年累月冲击出来的。我用锄头把表层风化了多年的泥土轻轻地挖松。只能是轻轻地挖,用力猛了容易把锄头的刃挖缺、卷刃。这样是要挨训的。弄完一遍,我把这些松土聚集在北边,开始用錾子敲打浅红的石块。这些石块经年日久,已经变得并不坚固。当然也并未变软。我蹲下身来,左手握錾子,右手握锤。扬起右手,落下,锤敲打着錾,尖锐的錾钻进石头鏠里,碎了一小片。再敲打一次,再碎一小片。我之前并未用过锤、錾敲打过石头,只是凭着感觉摸索着学着。慢慢地,叮叮当当地声音就起来了。
空山无人。我的耳朵里塞满了这种声音,似乎整个世界也弥漫了这个声音。
叮叮当当,叮叮当当……我认真地敲打着,努力地敲打着。
整个世界被敲打得呲牙咧嘴,浑身疼痛,血脉偾张。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,世界就安静了。
我随手扔掉錘和錾子,让它们躺在功劳薄上睡觉,或者聊天,随它们的便。太阳已经快下山了,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涂抹着最后的余温,轻风翻阅着满山绿油油的庄稼。天空沉寂,鸟语安然。
马路的转角处,远远地走来一个女孩。她是我的同学,正在复读。她的家在电桩土的上边还要上边。具体是哪儿,我也讲不清楚。这是她放学的必经之地。当她经过大坑时,距我只有十余米,我把头转向了另一边。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现在的这个样子。那时的我似乎有了小心思。

持续到第十天,父亲去验收工作。大坑里已经被我开垦出一片土地,大约有二、三平方米的样子。
“嗯,不错,咱们把它改良一下!”父亲很满意,并鼓励了我几句。
父亲找来渊兜,就近在电桩土里相对肥沃的地方取土,半泥半沙的那种土,装满两渊兜,我拿起带绳钩的扁担,挂好,一弓腰,直起来,晃晃荡荡将土担到大坑里。如此往返十余次,父亲才作罢。
我拿起锄头,照着父亲的样子,用力地翻土、和土,尽力将两种土质混合均匀。
“这是你这辈子自己开垦的第一块土地。今冬种上小麦,明年就有收成了。当然,我们家的所有土地,将来都是你的。你要好好努力,把庄稼种好了,照样也不差……”父亲站在地边,像是对我说的,也像是自言自语,语气里有一种很模糊很期待的情感。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父亲还是把话说早了,他当时不可能料到我会剑走偏锋。就在那年冬天,他带着我种完那一季的小麦后,参军入伍的消息传到了母亲耳朵。母亲极力促成了这件事。尽管父亲开始时强烈反对,但最终我还是穿上军装,踏上了开向北方的列车。
跑向绿皮火车铿锵有力的脚步声,宣告父亲对我人生的第三次规划夭折。
列车的轰鸣,将我从记忆中拉了回来。我随着人流出站,坐汽车回到红花乡群众村的老家。
父亲的精神尚好。见儿子回来了,分外高兴。家人一起瞒着他,没告诉他真正的病情。不知父亲想过没有:我一个月前刚回过老家,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?
父亲坐在床上,病痛难耐,有时会呻吟几声。癌细胞钻入骨髓的锥心,父亲的疼痛与忧伤,我都难以真正体味。我坐在床前,陪父亲坐着,不知该说啥,有时就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。
“爸,单位有紧急任务,要召我要回部队了。您自己要多保重身体。”
“好的,你回去吧。没事儿,过一段时间我就好了。”
父亲这话不知是安慰我,还是安慰他自己。
我伸出双手,第一次主动也是最后一次拥抱父亲。这是生离,也是死别。世间之事,还有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么?
待我第二年春天回家探亲,母亲已经成了孤身一人。我和妻来到屋后的山坡上,一座新坟新鲜的泥土已经长出了稀疏的小草,这是父亲骨头里长出的另一种生命形式。他已经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,与泥土浑然一体,以另一种永恒的方式回望这个世界。
我双腿一软,跪在父亲坟前,狼一般尖锐地嚎叫一声后,哽咽着泪雨滂沱不能自已……妻跪在身后,抚着我的后背,一句话也没说,陪着我默默流泪。
一年又一年,时间嘀嗒嘀嗒地缩短着我与父亲年龄的差距。父亲定格在65岁,既不会年轻,也不再变老。这些年里,我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工作中努力打拼,靠着父亲教我的坚韧,靠着农村人的勤劳,拥有一个较为稳定而平和的心境,不再恐慌。作为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子弟,还能有什么更大的奢求呢?可我还是不敢看父亲和蔼的眼神,我怕辜负了父亲当年的期望,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长成了一株健硕的庄稼,长成了父亲喜欢的那种可手可心的庄稼的样子?
作者简介:
张向前,笔名阿若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河南省作协会员,鲁迅文学院四川班学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散文诗世界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等。个人作品多次收入中国散文年度精选。著有《难以忘却的空战》《鞍马尘》《屐痕处处》《秋水长天》,多次在全国散文征文大赛中获奖。




















